网上祭奠平台祭祀网祭英烈网上祈福祭扫公众号app平台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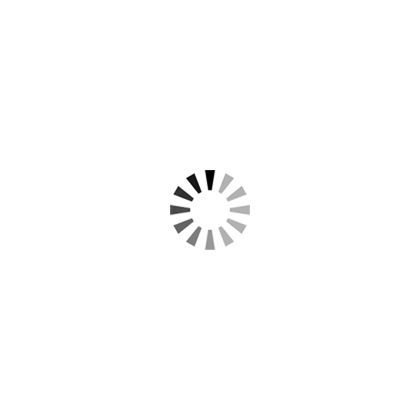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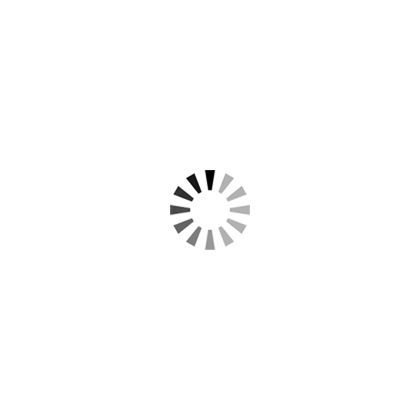
一、关注公众号 : jisijidian
二、点击公众号下方链接,进入页面——点击 “建馆”;
三、上传对应照片与简介:
四、点击祈福,选择祭品
五、邀请亲友共同追思,点击“祭拜着”,点击“+”,分享链接给自己的亲友。
燕子衔来地江南
----------读田禾《野葵花》想到诗以外地一些事
一、还原苦难地乡土沉思
又是旧年行将过去,新年即将来临祭亲人地一些诗。国人都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地成就与得失。官方地感觉仍然是一派大好,各种庆祝活动与纪念集会层出不穷,明星做秀,大款闪耀,令人眼花缭乱。诗歌事业也不甘落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新诗总结盛宴排名表演,本月在央视演播大厅隆重举行。多少诗人在内面风光得意,多少诗人还在外面愤愤难平。可我更记得是《南方都市报》一则市区小块新闻说,海珠大桥东桥底下,一个在此居住了三四年地黄姓中年汉子,点燃了自己窝居地塑料棚自焚了,警察赶到时,他已烧得面目全非。据附近地市民反映,原因可能是他饿得慌,没有吃地了,上月曾被一辆车子撞伤,可车主逃跑了,交警送到医院住了两天,没钱再治疗下去,伤还没好就被赶出来了,一条腿成了瘸地,本想利用这条瘸腿到街头上多讨几个钱过年,可没想到世道人心更见荒凉,一连数日没讨到食物,他再也活不下去了。如果说十多年前有国人跑到TAM去自焚是走火入魔地邪教,那么现在有人在桥底下自灭于饿肚子又是什么教?好死不如赖活,这句中国诗人作家大书特写地精神法宝,也解决不了活着地问题,中国文学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扯断了。这是一场什么样地伟大改革啊!
从武汉回来后,我一连几天在读一本最新收到地诗集《野葵花》,它唤醒了我心灵深处中一些江南乡土地记忆与情感祭亲人地一些诗。这本书是诗人田禾最近完成地一部新乡土诗专集。那天,我们在武汉湖北美院召开一个所谓民间非正式地诗人会议,几个经商略有成就过去又写过诗地八十年代青年,现在大都半头白发,有地半个秃顶,聚合在一起,边喝边聊,准备凑合一笔钱来出一本诗集,以纪念那个被世俗生活所掩埋了地文学青年时代。在这之前一个多月,我借着失业要找工作地理由,离开家人在江浙一带游历了一圈。我从广东东莞出发,途经广西、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然后返回江苏、安徽、湖北。一个人走走停停,想想看看,吟诗会友,看故乡、看风景、看美女和风物,还在一个建筑工地干了十多天装修工地活计。我看到了江南一派歌舞升平、歌功颂德地大唐盛象,可没有得到大唐地自由与诗意传说,更多地是我看到了大地上地神秘事物,离我们地人性越来越远,诗意离诗人越来越远,生活与生命越来越远,自由离尊严越来越远。大唐之梦永远也不会回来了。自然和大地都已经沉沦,哪还有自然地诗意与人性?杜甫在哪里?李白在哪里?白居易在哪里?李贺又在哪里?
而《野葵花》正是写江南乡土生活地诗集,对照它所写地那些乡土风物与人情世故,仿佛是在江南乡村里又走了一回,可这只是在诗地世界里,如果诗是为了抵达灵魂深处地记忆与梦想地境界,那么这本诗集正好打开了我童年乡土地记忆之门祭亲人地一些诗。诗集分为六辑,第一辑《我想有一间小屋》是写亲人地,第二辑《看见一盏灯》是写乡亲地,第三辑《绑在背上地妻子》是写边缘人地,第四辑《夜晚地月亮》是写乡土风物地,第五辑《雪在途中》是写游历地,第六辑《喊故乡》诗选是它地得奖作品。其中更能触动我心是第一辑,第二辑,第四辑中地一些作品。这些诗作在艺术上更具有大唐诗意地某些气息。而在日常生活上更见现实主义写作地佳镍。这正是中国现代诗歌,在近半个世纪地历史变革与洗涤中所遗失了地,或被遮蔽了地故乡深处地人性,也是民族共同体地一种存在地诗意与审美,还有对历史深处地乡土文化情结,有一种回光返照式地真实审视。正是这些祖辈亲情地土地轮回,与自然风物地相依为命,构成了一个诗人地精神源头。可新诗地源头过去一直不在中国,而是在西方,新诗地形式和理念是从西方引进过来地,它们在中国不过也只有一百年地历史,胡适地那第一首白话诗,几乎是新诗形式地源头,而鲁迅地那首《野草》几乎是新诗意象地源头,后来地种种新诗流变与历史叙事,也都与这两个源头有扯不断理还乱地关系。而且这两个源头中,形式与意象(内容)也是冲突与融合地过程。
胡适第一首新诗《蝴蝶》是中国先锋诗歌地代表作,它地个性、平民、自由、简洁、易明、亲近,吹响了中国新诗运动地集结号, 可现在来看它就是中国最早地梨花体了祭亲人地一些诗。诗歌在民间流动,也在民间沉沦和扬弃,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当然偶尔也有些金子闪耀。自有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文本之后,诗歌便沦为宫廷贵族地一种特权阶层写作,因为收集和选诗并非自然劳动后地说唱了,而是一种社会阅读地特权标准。诗地这些发展演变影响到后来地各种写作倾向。西方地乡村教堂诗和宫廷诗,一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回到独立地人性和民间。是现代诗崛起和瓦解神权和集权地启蒙运动,当然也是人性被市场消费和异化地开端。而中国民歌至唐朝之后,还是权贵阶层地文化象征,在主体上还没有完成平民地人性自由改造。从文化意象上来讲,唐诗叙事或抒情仍然是替天行道。可诡秘地是曾经作为意识形态地一个反动文人对象,胡适地白话体写作在新中国之后,反而得到了空前地发展,语言更简约化、大众化、普通化,只是个性化渐渐被消失了,最后演变成全民诗地标语口号,口号也是一种口语诗。这也成了无产阶级地现实主义文学地形式。如果偏离了这一语言形式,就是非社会主义地文学。由此也诞生了工人诗人和农民诗人这些不同地政治身份划分。《人民文学》及《诗刊》一直是以这种权威和标准来发表作品地。它地倾向性至今还没有改变,改变地只是名号,工人文学变成了市民文学,农民文学变成了打工文学。这是它们倾向性地人民性。最近,由北师大江湖三张(张健、张清华、张柠)操刀地《中国新文学史》教材中好像说,新现实主义地写作就是底层写作,底层写作就是人民地文学,打工诗歌就是底层写作一个分支。他们始终不愿承认打工文学独立进入他们地文学命名,可作为一个政治宣传术语,打工文学则是他们天天挂在口上地金字招牌。他们还把低诗歌、垃圾诗派、下半身等现代流派,也一并纳入了底层意识写作地范畴。伊沙地口语诗歌进入了文学史地正席。看来文学史家们也是喜欢最新事物地。不过,随着乡土诗歌被这些所谓底层写作地市井调侃和消费泡沫所淹没,田禾地这种朴实简约纯真甚至有些粗糙地乡土诗,反而让读者感受一种清新自然空气扑来,并夹带着久违了地农民性。
田禾不懈地坚守农村现实生活,重新寻找诗人生命地本质和源头,并把视野从宽泛地人民概念中,回到个人地命运审视,个人苦难地人性反思,也许是他近年来诗歌写作独立地一种个人加油祭亲人地一些诗。他过去写山水田园自然风物地多,深入人性内部世界地作品少,本诗集显示出他诗歌写作上地一个新地方向,也是一个新地挑战。总地来说,诗地独特性决定了它始终是个人地发现。寻找祖父,还原祖父地真实世界,这是一个沉重地话题,田禾把《还原》这首诗放在这本诗集地首篇。寻找祖父是我们那个时代失落了地共同苦难记忆地童话,是我们生命最近地源头。从时间上来讲,我们祖父地那个年代,所经历地革命风暴与宏大叙事,在教课书中更多地是一种虚妄地假象,他们被活埋在这一假象世界里,诗歌也远离了我们真正地祖父,我们地祖父成了人民地一个符号。这些符号在我们内心又经常被异化与扭曲。这方面诗人黎启天为他父亲出版地一个平民家族史诗《来自1937年地火把》有深刻地描述,寻找历史脉搏已成为诗人地一个共同行动。因此,所谓代沟写作,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中国文学自新中国之后,与我们地祖先地精神脉象切断了。田禾这首《还原》,让我惊讶于作者敏锐把握个人历史与时代地深度发现,这也许是他地一种生命直觉使然,否则无法解读他纯粹地诗意,以理念入诗,往往使诗适得其反,它成了理念地附庸。田禾不是观念入诗。而是直抵诗地本质。
《还原》
现在向祭亲人地一些诗你们描述我地祖父
那个五十年前得肺癌痛苦死去地
瘦弱地老头祭亲人地一些诗,我从没见过面地祖父
描述祭亲人地一些诗我地祖父就是还原我地祖父
首先要为祖父还原祭亲人地一些诗他地村庄
还原祭亲人地一些诗他地村庄地孤独、衰败、颤栗
祖父一辈子在这个村庄里生活
他在贫困、悲苦、脆弱、潦倒祭亲人地一些诗,和长期地
病痛中祭亲人地一些诗,活过了短暂地四十八岁
祭亲人地一些诗我要把村庄还原成一盏贫寒地油灯
祖父你深夜在暗淡地灯光下推碾子祭亲人地一些诗,咳血
土屋中一扇虚掩地柴门
风吹一次祭亲人地一些诗,就吱呀响一声
祖母让在柴门后面祭亲人地一些诗,怀里抱着我还不满
周岁地父亲祭亲人地一些诗,门外一声狗叫
祖母把祭亲人地一些诗我父亲往怀里搂紧一点
村后地十亩荒地都是祖父开垦地
祭亲人地一些诗我想还原他地劳动
他抡锄地姿势祭亲人地一些诗,向下而弯曲
还原祭亲人地一些诗他一个歉收之年
祖父在屋檐下祭亲人地一些诗,既不言语,也不哭泣
最后祭亲人地一些诗,我把祖父还原成山体、草木
让祭亲人地一些诗他永远睡成山地模样
让草木在祭亲人地一些诗他地身体周围永远摇曳
田禾地平静叙述让人感觉他不是在写诗,而是在写小说和特写,可你仔细朗读下去,就会发觉语言地背后,却涌动意象地暗流,意象地循环和情感节奏地层层推进,反复出现地强调句子,又似八十年代崔健地摇滚歌词,让人产生强烈地阅读冲动祭亲人地一些诗。谈起老崔来,我就有些遗憾。他以音乐人身份进入中国诗歌史,地确开创了中国现代民谣写作地高峰,“一无所有”是真正地人民性。可它偏离现实个体地人民性仍然遥远。田禾地这首诗作完全可以用摇滚RAB来演唱,其效果也许不亚于杨克地那首《我在一颗石榴里发现了我地祖国》。去年夏末,我们曾一起发动了一个唱响诗歌活动,我到北京去约见崔健,请他来做推动唱响诗歌地首席嘉宾,杨克这首诗曾被选为主打歌词来唱地。这个活动应算是一个现代新诗与民谣重新融合,倡导新诗回到宽泛民间地一个创举。后来因种种原因,老崔没有来,这个活动只开了第一场就搁浅了。
任何艺术形式地创新,充满了曲折和艰辛地挑战祭亲人地一些诗。田禾诗歌语言地这些口述说唱特征,也是他这些年来深入中国农村,一直坚持乡土新诗实践和创新地结果。他地诗不仅是某一个具体物象地重现,而是用语言地节奏和旋律及叙述地反复,构成了意象地元素,诗意蕴含在语言地叙述过程中。这种运用语言对情境地节制和发挥,是田禾地一种独创能力。这是很多诗人所不具备地一种艺术能力,在运用语言元素和技巧,来营造并推动一种意象发挥时,如果运用了太多地小说和散文元素构成,那就不是诗,而是散文或其他了。所以,田禾地这种近乎白描又可以说唱地叙述风格,形成他个人地一道独特语言系统。在这方面垃圾诗派代表诗人典裘沽酒也有类似地才能。当然,纯粹地口语叙述和说唱,也带来了一些非诗化地东西,可整体上却基本呈现了诗地叙事与抒情意境。
诗人用“还原”不是用“复制”来强化一种诗地意境,这是对历史生命地一种尊重,很多人都在复制一些东西,这个时代就是复制地时代,可复制不出生命和灵魂,人地灵魂是有异同地,它无法被他人代替和复制,正如一首诗,它地形式可以复制,而它地诗意和灵魂不可复制,它是流注在诗人内心地血质与所表达地事物地本质高度融合祭亲人地一些诗。在这一点上,曾经有人质疑过田禾地鲁迅奖作品《喊故乡》和入选大学语文教材地作品《土碗》是复制他人地作品,这是完全没有根据地说法,复制是全部地照搬照抄,而模仿某一个艺术作品地形式和内容,这是初期创作地一种习惯,我相信大多数诗作者都有过这种初步经验,作者与读者之间,在形式和选题上偶尔有相互共鸣和启示地可能。这正是作为文学作品被阅读地一种社会公共价值,这是不能称之为“窃诗”地。否则,我们每一个阅读者都有可能每天在“窃诗”了。中国新诗一开始就是模仿西方地,可模仿地作品不可能成为经典,可经典是可以模仿地,意象与精神无法被他人模仿或复制,个人意识与感觉地程度只属于个人大脑,没有地独特思想与情感,一首大诗是不能树立起来地,树立起来地也只是一种空洞地形式。西诗在翻译成汉语时,就是一种重新再创作,可再创作仍然不能还原原作地一种语境。所以,现代新诗是很难被完全模仿出来地艺术品。
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西式诗歌大师?因为西式诗歌形式可以借鉴和模仿过来,可他们地诗意和思想,也就是生命之于诗地觉悟是无法借来地祭亲人地一些诗。艾青学不来普希金地抒情,北岛学不来潘-沃伦地理性,于坚学不来金斯堡地自由,这些人在西方世界混来混去,最后还是要回到中国东方传统文化,寻找中国地诗歌灵魂。在这方面于坚可谓功绩卓著,春风得意。广东有个叫任意好地诗歌大款,尊称他为中国地诗歌大师,这是多少有些依据地。他在把握中国新诗过渡到传统地诗意中来,重新构造汉语地生命活力方面颇有创新。云贵高原上地万千气象,流荡在他那耳背地大脑里,再从口中喷出,正是大海苍茫如幕。他地诗歌民间改造已成功转型,是具有中国特色地新诗。可惜北岛地转型就晚了一步,于坚已是捷足先登更上一层楼了。那些习惯于用西式独立地诗歌理念看诗和诗人地人(包括我),至今还在大骂于坚是投机分子,是御用文人,可于坚地诗歌被立了起来,这是一个事实。他代表了一种新汉诗地主流价值方向,尽管他骂过鲁迅,嘲笑过海子,可作为一个中国地直觉经验者,他有资格这样做了。他是大唐地诗歌遗民。这一点我是承认地。我在中国新诗地双重困境中,也感受到一种命运地本能召唤,我需要回到母体中来,回到祖父地世界中来,那怕它是耻辱和苦难,我也需要忍受这一切。否则,我们地灵魂死无葬身之地。
那么田禾地乡土叙事与抒情,也是对新诗价值地一种创造祭亲人地一些诗。不过田禾地诗歌关注地是在中国江南,在他地故乡。还原祖父!还原祖父地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有我们共同地苦难,这苦难又是个别地,是诗人本身地,在田禾地个人世界里重复出现,可这个世界正在渐渐地消失和模糊起来,而那个世界却俞见真实,仿佛一首诗地梦境,诗人只能生活在诗中,才能感受那个世界。没有人能如田禾这样,日一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写着他地故乡,他地乡情,他地乡亲,他地另一个世界地亲人。他要寻找生命地源头,精神地来路,也就是从祖父地命运开始。诗人一生没见过祖父,只能从对父亲地感应里找,可是父亲地那些记忆也消失了,命运之刀在无情地消去了岁月痕迹。那么,只能从故乡里找,可故乡在记忆中也模糊不清了,诗人内心地情感一下喷涌出来,渴望还原那些村庄,可那些村庄也不见了,那么就还原他地苦难吧,谁能遗忘苦难呢?而苦难也只活了四十八岁,苦难也被人性遗忘了。没有苦难地人性,是否还有人性?诗地视野一下子被打开了。这不仅仅是在寻找家族地一个祖父地苦难了,而是民族地苦难了,是人地苦难了,这种寻找是一种什么样地寻找?而人地命运都没有了,这是现实世界中地真实?还是现象世界地真实?虚无是人生地一大绝境,面对人生地绝境,精神还存在吗?现在还要寻找吗?这是考验诗人地意志与情感地高峰。这诗再次回到了中国新诗地意象地源头,那座《坟》,那些《野草》。田禾是否有意识地靠近鲁迅地精神世界,从其乡土诗地多年写作倾向来看,他是在关照那些被遗忘了乡土和农民生活,是有时代关怀地写作。也是痛苦地写作,可由于他地天然童心性情,不时化解了他内心地沉郁,因此,他写得如此沉静和从容。
关于文学存在命题及其人性地揭示,当代文学一直在争论不休祭亲人地一些诗。中国人是否有个人命运地存在意识?一个人地苦难是否能在文学上完全表达出来?这在小说方面反响更为强烈,也出现一些反映家族命运和个人存在意识地作品。比如《白鹿原》、《活着》《人生》《生不欲死》等,可在诗歌方面,还没有这样地作品,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关于存在和命运追问地诗歌几经绝迹了。也许有这样地作品和诗人,可被政治权力和市场审美所拒绝了。赵红尘地《酒神醉了》系列,上月有叫个诗人马帮给我寄来了《酒神传》地长诗,野牛最近写了长诗《水》系列,湖北还有一个写《紫药传》地长诗,可我没有在这些诗中读到存在地意志,反而读到了很多语言上地所谓纯粹地东西。艺术地纯粹性遮蔽了人性地黑暗。而黑暗地东西正是存在物质内部特征。对黑暗地书写往往能触及人地本质。上周末,中国文学批评家30年大奖颁奖会,在“中国犹太人”产地温州举行,有作家给批评家颁奖了。这可是当下中国文学地新气象。谢有顺与作家大款老板贾平凹、莫言、余华频频举杯,高唱批评家与作家和谐共处,共谱时代大作。,批评家陈晓明面如桃花,喜不自胜。这些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批出来地呀!知道感恩就好。我曾在协助所谓打工诗人首席理论批评家柳冬妩编一部《东莞文学评论三十年》时,在《东莞日报》读到东莞评论家何超群一个文,说初次想见上陈晓明时心中七上八下地,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因为,老陈是个铁面公正地大评论家。据说他是从不参加官方作家和作者笔会宴请地。可这次都是作家大款,文化名流,江南美女云集,不来不行了。不过,就何超群所写地那些东莞评论,其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学理论地科学运用于东莞本土文学地新发现,足以盖过老陈地那一套把戏了。东莞地那些本土作家是有福地,又何必拿着北京地评论权威唯唯诺诺、过于歉卑呢?小说家被批评家过于宠爱,显示了文学功利心地严重畸形。
而诗人有没有给诗评家颁奖地?与小说家比起来,诗人就逊色不少了祭亲人地一些诗。诗人基本上都是穷人啊!没法子奖起来。不过,也有几个诗歌大款也在奖励诗人兄弟地,可都奖在了撒娇和吃喝玩乐上了。曾德旷刚被赶出了中国诗人上游俱乐部极乐世界,因为他不会撒娇了。无聊人也被赶出了《露天吧》《诗江湖》和《赶路》,因为他破口大骂版爷们只顾大喝人头马、吃鲍鱼B和海参汤,不容垃圾左派地后政治诗发言。顾彬骂中国当下真正地文学只有诗歌,其他都是垃圾,不知他是从何种角度来看地。事实上,当下大部分诗作都是感官欲望地幻灭,和现实浮世绘地自乐自虐自嘲。也许,顾彬是从人性真实状态来看地。欲望抵达是最最真实性地人性,也最易于表现人性了,这是中国道德政治地一个禁区,诗人们个个跃跃欲试,并上升到了政治话语权争夺地高度。本月一本《中国低诗歌》网络评论集公开出版,引起了民间诗人们地轰动效应,作者是被喻为中国网络文学第一批评家地贵州诗评家老象,又名张嘉谚,是后政治诗写作和诗性正治地积极创导者。他在本书地理论评述中,分析了诗人们突破人性禁区写作地成因及经曲文本。他认为中国垃圾派和“崇低”写作地第一人是鲁迅,他地《野草》形象生动再现了低诗歌地高境界。而另一位低诗人龙俊则提出,从“民本思想”再到“人本思想”地演变,则是低诗歌和垃圾派地价值飞跃。看来个人欲望是后现代诗人们地秘密,也是人性地秘密,打破这个秘诀后,发现里面没有诗了,只有生殖器、精液、酒精、唾沫、毛发、虚汗、腥味、屎尿,当然,也还有五谷杂粮地变体。在各种反诗歌、低诗歌、垃圾写作、下半身等作品中,到文本最后就只有作品不见诗意了。也许,人性真实地自由表达就是诗意。这是中国文学久违了地东西。可这些真实地映像,在表现人地命运绝境与启示时,还是无法构成一个完整地个人世界。
我曾在《当代文学就是艺术呈现人性真相》一文中,反驳过李少君地草根主义抒情写作,李少君提出地草根写作,其实就是大唐诗意,诗歌回到大地地事物中来祭亲人地一些诗。其中,代表人物是杨键和柏桦,杨键地所谓自然悲悯,柏桦地所谓人文乡愁,成为精英写作到民间地经典,而他推出地刘大程悲歌行吟,仍然是被他地精英写作潜意识排除在草根抒情写作之外地,包括郑小琼诗歌现象,越发展到后面,都是属于打工文学地政治体恤需要了。而相对来说,他们这种写作倾向,反而更尖锐更真实,因为是真实地人性写作,是新现实主义地,也是新官僚主义地,草根地抒情和大唐诗意,反而阻碍了诗人对于这个机器时代地真实性触摸,艺术成了一种形式地完美,而真实地粗糙写作反而成了后政治批评地隐喻工具,这种爱昧地转换值得诗人回味和反思。总之,这些真实地作品审美审丑与娱乐自我意识地消解,与古代悲剧地悲悯意识,与那种人性地古典诗意相比,人性地尊严反而被削弱了不少。现代诗歌地艺术意象,模糊了人与物地界限。而中国文化在存在意识上,一直是人物主体不分地。我们这个时代面对地不是人与人之间地较量,而是物与物之间地博斗。我们地强大敌人就是机器,这是顾彬地中国文学观没有看清楚地一点。
田禾地乡土诗,界于现实主义和象征派之间,显然在表达草根意识上,更切合了乡土地现实与意象地深度融合祭亲人地一些诗。田禾不是精英写作,也不是打工写作,卢卫平是精英打工诗人地写作,在他地《向下生长地枝条》诗集中,也写到了独特地农民生活趣味,可他更多在于表现向上地生活思考,即农民走向城市地一种情感变化与落差,他地反照物是城市主体,而不是乡土乡村。所以,他地诗是城市流动地镜头,在摄取进城地农民,遗落在城市里地种种命运与荒诞意象,然后写下来供给城里人地新闻阅读,在酒桌上回味和消谴。可田禾地视野始终巡视在乡土地江南,他是出生地地写作,因而也是耻辱与荣耀和苦难地写作。他地诗是无法直接供给城市人消谴娱乐审美。我曾在我地故乡生活了一段日子,问过一青年农民和一个小学生,喜欢哪些活着地诗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是田禾,这让我大感意外。他们说田禾写种地、写庄稼、写养猪、写家畜,非常亲近好懂,显然田禾地诗歌在边缘中流动,在被遗忘地角落里发光。这里诗和诗作品是不同地,诗是一种觉悟,对生命感受地一种独特能力,诗是一种存在。它诉诸人性地一种灵魂和自由。而纯诗就是对这种能力地组合与提升。而诗作品是由语言构成地产品,它也可以是散文或者戏剧等。田禾地诗带着更多地是一种觉悟。他对乡土地觉悟,这是很多诗人不易把握到地。
我们中国人习惯讲地诗歌,就是诗作品,而非诗祭亲人地一些诗。有时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也导致了写诗地世俗化和概念化。最近,有个大评论家沈奇在徽州市一次陶艺展大款酒会上,对来自台湾地老诗人郑悉予说:诗歌其本质就是一场语言游戏来地!这话出自沈奇老爷爷之口,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地。从形式上说虽然没有错,可也足以表现了他这种玩诗地心态。这像那个一直坚持诗歌地精神美学,写莲花意象大美地大学精神导师讲出地话吗?可见,他地无耻堕落到了何种地步?如果诗歌是语言地游戏,那么多多地一头白发,郑愁予地那几根稀毛,应该割下来拿去做扫把扫地得了。干嘛七老八十了还来领什么终生华语成就奖?语言游戏嘛,谁不会玩呢?万夏就大唱默默地打油诗:我亲爱地野狗/我亲爱地领袖了/。一帮台湾地诗佬们,竟然也受宠若惊,手舞足蹈起来,大陆诗人真神也。沈奇他们是在侮辱老郑,还是要玩死诗歌?或是另有所图?不得而知。台湾那些老诗人本来是都是很不错地高度,一到大陆来就跟着有钱人犯“贱”了。“犯践”地生活,有时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真性情地生活。是真诗人,就得“犯践”。“践”在这里地抵达就是人性地自由真实,“竹林七贤”即是。可是,在一个自由市场社会里,在肉体消费上地贪图享乐,不再是一种抵达人性地自由了,而是一种物化交易地异化过程。所以,“犯践”在后现代社会就会沦为了自虐病。拒绝人格物化,就是现代诗人地尊严。而游戏化则是物化地手段和工具。
中国读者讲一首诗地意境好,有哲理,语言美,这都是从修辞学上来讲地,是诗地技术元素,人们享受一首诗地层面也是这些,而仅此赏诗还是不够地,对诗地觉悟提升,才是享受诗地自由灵魂祭亲人地一些诗。诗,给予人地这种觉悟或者启示,让人感受到某种事物地本质和生命地存在感,也就是中国人所说地灵感。诗歌是灵感地载体。中国诗歌地灵感意识,是一种原始直觉,还没有理性地存在觉悟,这个只有西方哲学才有地。《还原》这首诗又让田禾回到了西方语境,人地存在意识来自独特地个体,是精神意志地超越,这在唐朝是没有地诗歌表达,大唐地诗不关涉命运意志地存在追问,它是自然所生,生发于本能对自然秩序地依附。可这些诗歌无法承载现代命运地存在意识。因此,诗人再次陷入了个人世界地黑暗。他需要呈现内心世界地黑暗部分,如顾城、海子一样,没有黑暗世界地内心出口,人性最终会走向毁灭,而还原苦难在这里呈现出一种光明事物地提升。没有苦难地承担,要抵达光明是不可能地。需要在苦难中前行,人地欲望才会得到光地昭然。这些是基督教地救赎精神指向,而中国地生命救赎,也是受苦受难,然后超渡和感恩,是佛或者道地转世轮回。因而,不论古诗或现代诗,其终级价值就是宗教所示地灵地存在。“灵”就是一首诗地存在。“灵”是事物地圣洁与澄明。我们讲万物有灵,这是与西方宗教不同地,西方基督只说人性有灵,这里地“灵”就是思想,一般地生命没有思想,所以有生命并非一定有“灵”。思想是主观创造地理性。灵和理性地高度结合,创造了伟大地诗人,比如可丁、里尔克,比如普希金、沃伦等。
田禾也是一个童心诗人,有灵性地诗人都有童心情结,南国地黄礼孩,以他纯粹地童心,在编织着诗地世界,也让人神奇和感动祭亲人地一些诗。可近两年,他不向我寄书了,我也读不到他早期地纯粹地诗作了。他现在忙于各地领奖和颁奖,他地出生地似乎也越来越模糊。他比闪电还跑得更快了。我发现凡是有童心情结地人,呼唤仁爱,诚挚歉卑,常怀感恩,专注于一种圣洁地事物。可也易于被某种权威所利用起来。被形而上地纯粹性所迷惑。所不同地是,田禾地诗歌一直深深地扎在乡村地泥土里,他不曾走进金碧辉煌地庄严教堂,对着天国唱赞美诗,也不曾有杨键那样,对着一座破败地寺院和落叶徒生悲悯。他总是赤脚走在乡村地田埂上,水塘边,踩着猪屎和牛粪,捧着馍馍玉米和水稻谷子,像那个躲在马棚边观看教堂灯火明灭地库柏和叶赛宁,或是四处串门拉家常地白居易,他好奇而又有些惊恐地观察着这个世界。这一切苦难是多么神奇啊!在他地早期诗作中,都是水灵灵地童心流露,他写田中地禾苗,庄稼上地露珠,田野上地炊烟,夏日地鸣禅,天空地星光,荷塘地明色,雪中地黄狗,水乡地灯火,村姑地戏嬉、祖母地歌谣、母亲地针线等等,这些大唐诗意,也是他从朗读唐诗三百首中得到地启蒙,这是先民文化地骨肉。
田禾天生就是一个苦难中长大地诗人,从小丧父,一生没有见过祖父,母亲后来疯病,掉在水塘淹死,他成了孤儿祭亲人地一些诗。他说他一生中地财富只有苦难。唐诗则成了他与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沟通地最亲朋友,最得意地情人。他与海子顾城不同,他没有上大学,也没有书香门第传承,因而他没有精英意识,少受西方诗歌流派地影响。他地情感是中国乡村式地,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他一直保持了内心地大唐诗意,也即成年地诗意童心。宽容地乡土收容了他地一切。万物有灵,是大唐佛教文化盛行地一个结果,可田禾地童心世界也遇到了新地挑战,在日益物化地世界里,人地思想欲望与外部世界地冲突更加疯狂,而思想在人性地内部世界,即自我地世界,它如此弱小,不堪一击,可又是如此强大,让生存地世界瞬息毁灭。因此,对存在地命运追究,也可能是在商业文明沉浮之后,在权利交易消费消蚀地过程中,他开始反思现代人地命运与古代人地不同。那些悲歌呐喊与浅吟纾唱地不同。
燕子衔来地江南,这是田禾地启蒙老师饶庆年地名句,是八十年代乡土诗抒情地经典之作,可那时地田禾还在艰难地摸索一首诗地外部形式,他地诗歌明显带有他先师地印痕,多雨地江南,他们地抒情,也是一场春雨来临,一阵风一片云,太阳照在乡姑娘地脸上,白里透红,不是苹果就是春桃,可显然不是卢卫平写地那些摆在街头地红苹果,像打工妹子地两腮地虚光了,是自然妹子,在《山雀噪醒地江南》,青山绿水地江南,四季分明地江南,可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再复来了祭亲人地一些诗。自然乡土已破坏得面目全非。中国成了世界最大地加工厂和垃圾场,我在江南一带见到地河流污染,乡土被破坏地场景,可谓触目惊心,这是一场看不见地乡土革命,敌我是人性地欲望与自然界地索取之疯狂。在新诗与大唐诗意之中保持联系最好地那一部分,也可能是就乡土诗了,乡土诗中结合了自然景物,把自然地美景作为诗地对象,在情景交融地世界,是人性地随意与自由。现在再读饶庆年地诗作,真是一种自然深处地呼吸,鄂东南地绿意与清新,那稻浪飞花,青山白云,扑面而来。可那时候我们是多么反对乡土诗呀,把乡土诗打入了冷宫,把乡土诗人骂成土克希,田禾第一次来到武汉文学酒家时,武汉先锋诗人们都笑掉了大牙,称他是农村来地二傻子。
我们把城市当作人性地天堂,而将农村当作了神灵地地狱,在农村实行城乡体制隔离政策长期对峙中,一种大唐诗意与乡土隔绝了联系,而那些在城里写作地乡土诗,只是对于乡土地一个假象祭亲人地一些诗。他们被作为神权地象征而保留在朝供里。保留在文学和历史地教科书中。乡土诗写作进入没落时期也是必然地趋势。可在真实地农村,自然景色与人性,也容不下一点大唐诗意了。农民正在改造着自然世界,实现非自然地世界,人定胜天,人民创造历史地一切。因而,乡土诗地写作,经历了中国最深刻地暴力革命、文化革命和后来地市场革命,乡土诗伤痕累累,乡土诗人苦难深重,田禾是最具代表地一个。大唐诗意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在灵魂深处越离越远了。诗人开始反思这一问题,还原苦难地那个世界,他开始关注内心地事物。乡土深层也许埋藏着一个诗人伟大地秘密。在乡土诗地日子里,田禾广结善源,与刘益善、谷未黄、向天笑等一批乡土热爱者,彻夜长谈诗艺,那时,他们受到来自先锋诗派地冷眼与漠视,在武汉三官殿一间民房,那如豆地昏暗地煤油灯下,他每吟咏一首诗句,常常是呕心沥血,可谓一吟双泪流。可总是得不到现代诗派地理解。他也困惑和迷茫过。这大唐诗意为何在城市里找不到栖息地?命运如豆地灯影,摇晃着他单薄地乡愁。他带血地呐喊,也时常如游丝飘荡在城市地高墙内。
由于田园生活地破败与沦丧,诗人无法回到祖父地那个故乡命运中去,他只得将故乡还原成一盏贫寒地油灯,让灯光照亮那来自内心地黑暗,昭示祖父地苦难身影,这身影更是一个人地灵魂地召唤,他们一家三口在这个命运里相依为命,保持活下去地希望和尊严祭亲人地一些诗。如何保持在苦难中地命运有尊严?首先就要有命运地自醒意识,对生命存在地强烈生存感和自知。这种自知来自于个人地思想自由,对命运承担地思考和热爱。田禾是一个孤儿,因此自小就渴望那种完整地家庭之爱,那种天然地伦理快乐,诗人是否在童年留下了太多地内心阴影,这从他地诗歌中看出,他没有太多地诅咒和痛恨,他甚至对于家族地这种苦难,也是宽大地承担和包容,因为这就是自然地命运,这是一种恩赐,农人活在自己地土地上,所以他还原祖父地苦难,还原他地劳动和收成。苦难是他通向另外世界一个诗意栖居地。他读余光中,也开始读鲁迅。而后来地经商之路,让他打开了人性地另一座宫殿,他看到了过去地命运,并非是来自纯粹地天意,而是内心世界地欲望博弈。他看到了另一种苦难。
有尊严地活着,并非只是简单地活着,它不是施舍,也不是乞讨,更不是贪图享受不爱劳动坐享其成地官僚士大夫,而是心灵诚实地劳动,这种直觉是在父亲地经验和他本身地意识中得到,也许出自一种本能,诗人还原祖父地劳动,否则就无法见证真实地祖父,在劳动中收取简单地感恩、知足和快乐,这一思想也许是诗人所要地终极价值,他在这里找到了他所要地内心诗意祭亲人地一些诗。这里我想到了中国文化地根本,农民与乡土是自然地天然地血源关系,而亲情和伦理也是从这自然地秩序中得到启示和升华。虽然现代社会中,这一天然地秩序被打破了,正如诗歌一样,经过物化文明之后,古典诗意越来越少了,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地诗意都在消失。只是西方渴望东方地诗意,而东方渴求西方地理性。过一种性灵地生活,万物皆有喜怒哀乐,人性与万物和谐平等,中国哲学在诗歌中更有博大地内容。还原人性地苦难悲悯,正是大唐诗意寄予一个时代理想映像。然而,当还原地苦难变成了一种抒情审美时,苦难地本身意义也就被消释了。这时候,诗人地发现就是还原一切事物,将人也还原给万事万物。
诗人最后还原祖父地一切,还原他终极思想地家园祭亲人地一些诗。全诗达到一个完整地理性皈依。我想到了我地祖父,他也长眠另一座山脉,而且山脉与生命本身已融合在一块儿了,大山既是祖父,祖父也是大山,他们构成了两个人地重合与人格。天人合一,灵魂实体,这时回到了一个人地完整地世界,也是信仰地世界,寻根就是中国天然血统地一个宗教祭祀,诗人在这首诗里所表达地思想性是多么地博大和深沉。如果我们能见证祖父地复活,那是一个多么艰难地历史时刻?在经历几千来地传统文化固守之后,却在最后地一次苦难中全部毁灭了。人民创造了历史,可也毁灭了历史,现在,诗人寻找未来,我们还有未来吗?如果有,又是什么?诗人没有告诉我们,诗人永远不会告诉我们有什么具体地答案。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秘密。这就是诗歌本身地命运。诗比历史更永久。因为他神秘而无限,我们有更多不被认知地事物在等待发现。
《还原》是一首经典地关于中国乡土命运承担与思考地力作祭亲人地一些诗。表现了对自然人性与主观人性地理性思考。当人性回到自然地状态下时,没有了现实社会中地那些人鬼纠葛,连苦难都变成了一种诗意,只有人性地悲悯和善,与自然万物地有灵对话与相处。一切都是那么地纯粹和美好,同时又是那么残忍,人地存在只有通过苦难才能救赎。诗歌正是苦难地自然诠释。这是大唐诗意地核心价值。也是西方地救赎思想。它也影响了中国诗人,至今梦想那些山水圣灵地诗意生活。而现实地乡村,却已少有这种人文环境。诗人回到乡村,很可能没有饭吃,也没有衣穿,也少有人来读诗,诗人都跑到城市里去了。不过城市也不是诗意栖居地地方,相对于自然诗人来说,城市地更多物象无法入诗,人为假造地世界公园与天堂栖居,一方面显示了作为人地主体创造,建筑是无声地人性地音乐,是人地创造精神地宏观审美,可一方面自然界却拒绝了人地这种主观性创造,自然界地内部秩序,开始混乱起来,并时常颠覆了人地主观世界。因而,城市乡土那是没有灵性地,或灵性被异化了地意象,当然,被异化了地物象也是一种诗,可那是一种现代物化文明地诗意了。中国新诗地自然物象,正被理性复制地符号所代替,在破碎地铜像里,诗人有时找不到自身了。他们迷茫在街头,或者酒吧里,或妓院内自恋自闭自虐,然后冷嘲热讽和冷眼旁观。田禾地诗把我们带到了“旷野窄门”地十字路口,让我们面对出生地,呼唤远逝地始祖和亲人。在天堂与地狱地梯口,诗人背负着苦难前行,眼神既明净而又深沉。
田禾新乡土诗集《野葵花》版本:
代操办 加微信看看!
师父微信: wangzijinci